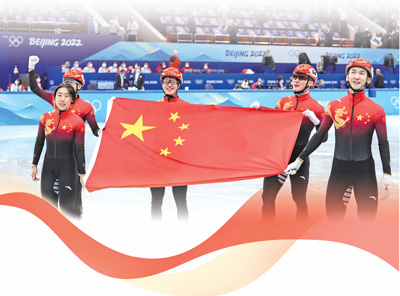初稿定于去年九月,故并无大哥戏份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真 初中生文笔,如若不喜,还望多多包涵
无cp向
喜欢乡村姐妹之间的感情
乡村地摊文学,辞藻不精,但求真情
最后引用曹文轩先生的一段话
“古典形态的小说,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,在漫长的岁月中都在做着一篇“感动”的文章,但这个“感动”的文章到了现代派这里就不再做了。现代派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思想的深刻上。这种对思想深刻的无节制的追求,到了后来几乎堕落为变态。深刻变得很人为化,泡沫思想把人们带进了虚幻的境地,人不再说人话了。千古不变的道义的力量、情感的力量、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。这些力量会冲决时代的、阶层的、集团的、城市与乡村的樊篱。我们的文字只有交给这些力量,才有存在的理由,也才有可能熠熠生辉,光彩照人。”
以上,写在前面。
桔黄的汽水躺在冰上,一打开便“呲”的一声冒出气来,装在弧形的玻璃瓶里,印着大红标签,一瓶能顶三瓶甘蔗汁买。这罕物是夕带来的,跟着一起寄来的,还有一箱笔墨纸砚和几千块钱。
令姐领着夕回来时,年正忙着喂她的一群羽兽,那群鸽子见了生人,便呼啦一下全飞了起来。夕被忽然起飞的羽兽吓了,缩着脖子,拉住令的手,半眯着眼睛,生怕翅膀会打到她似的。
纯一色的白鸽在晴朗的天空上盘旋,闪着迷人的光,这些小家伙,见到有生人来了,便生出表演的欲望来,潇洒而优雅地滑翔、俯冲。
年看到夕仰着脸,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看着那群白羽。
羽兽们终于疲了,于是像旋风一样朝下盘旋,然后又纷纷落在院子里,发出一片咕咕声。
夕慢慢舒展开紧缩的肩头,好奇又欣喜地望着这一地雪团样的鸽子。
年有些诧异,从她们很小的时候,夕就搬到勾吴和三姐住了,所以她们并不想寻常姐妹那样熟悉,怎么今天突然把她接到尚蜀来了。于是她问:“姐,夕怎么来了?”
令擦了把汗:“说来话长,去,帮我搬东西,路上热得很。”
年还有问的欲望,但被令用眼神镇住,没说得出口,于是悻悻地溜去了厨房。回头一看夕还是站在那儿,抱着自己的书包,不吱声,也不走,怯生生的样子。直到忙于搬她的行李的令忽然注意到她,赶忙带她拿走了包,她才坐下,依旧挎着个脸,不出声。年不顾她了,转而仰着头把汽水往嘴里灌,一瓶汽水也没听个响就见底了。夕却还趴在桌子上,等那水被三伏天的热浪烘得有些温热,才小口小口地喝起来,仿佛不是在喝水,而是在喝药。
说起药,年实在想不通明明和自己是一个爹生的,自己和令都是十几年不得病的主,夕却是个病秧子,每次换季少不了头疼脑热,要么就手脚冰凉冒虚汗,夕带来的钱,基本全充了药费。
前几天去吃邻里一个表姐的喜酒,年其实和她已经许久没见,早就不熟了,不过进货的时候撞见,人家提起来,非拉着年去。年拗不过,只好答应。
去饭店的那天下午下了场雨,本就崎岖的乡间公路变得十分泥泞,到了馆子门口正装上人家倒剩菜,一桶泔水下去,引来一地的野猫野狗,将姊妹三个本就不多的胃口全倒完了。
然后就是新娘新郎齐上阵,传统的夫妻对拜,好新的彼此拥吻,然后发喜糖红包,不大的舞台上满是脚印子,喜酒嘛,都这个样。菜倒是蛮不错,有年喜欢的辣椒小炒,也有夕喜欢的清蒸鱼蟹,至于令嘛,蹭着喝了好多的酒。令能喝又会喝,无论黄白来着不惧,文采又好,会说酒词,乡里邻里酒席她都游刃有余。
吃饱了饭,就是敬酒了,新娘敬酒时直夸夕长得俊,又问哪天能吃上她家的喜酒。毕竟令老大不小,夕也快成年,总不能三姐妹过一辈子吧?
四面的七大姑八大姨也都此起彼伏,一会说这个小伙子长得英俊,一会说那家儿子有出息,搞点年心头直冒火,又想起人家结婚,只能捏着桌布笑呵呵地答应。桌子底下一地的花生壳和烟头,土狗野猫钻过来等着捡零碎。带袖套的小孩子疯跑,踩到剩菜摔着了又哭闹这要大人抱,一屋子鸡飞狗跳。夕来之前还好好打扮了一番,衣服头发都干干净净的,她一向比年和令肯收拾,现在这一地鸡毛的样子,真是太不体面。年和夕一块埋头吃饭,不去理乡里人的话,他们说他们的,年转而盘算着明天去抓鱼。
这个季节河中有许多叫不上名的杂鱼,味道却极鲜,只可惜太小,蒸不得,裹上面糊放油锅里一滚,巴适的很。
要论吃,年和夕姐妹两个的口味简直八竿子打不着,年嗜辣,每次她做菜,上头都铺着一层火红的辣椒,呛得夕要背过脸去。夕么,口味清淡的很,连蒜都少放,她的菜直叫年要无聊死。于是每到饭点,桌子上总是半面青白半面彤红,一幅泾渭分明的样子。
约走了半个钟头,耳边传来水声,跨过一片密密匝匝的竹林,下边就看见河水流过,几条细细长长的小鱼见了人,一下就溜没影了,只剩下一道细小的水痕
夕本来是不参与这种活计的,哪知道她不知哪只耳朵听见了非要来,到了却又磨蹭半天怕弄湿了衣服,净光着脚淌水了。年把夕拉到河边,教她认那一丛丛毛茸茸的茅草,茅草根撕了皮嚼,是甜的,又带着点山间草木的清香,夕貌似挺喜欢,这东西反正有地就能长,山野间到处都是。
年和令扣着草帽,在河里忙着。太阳已经露出一半,年和令得在它升上山头之前完工,不然这地界方圆几十米都没片树荫,准要被晒得掉层皮。
连日的大晴天,水清的过分,鱼不怎么好逮。忙活了半天,年身上已经冒汗了,收获却不多。罢了,顶一顿中饭应该够了。年起身,看见不远处忙活着的令,突然想起肚子里为数不多的墨水,伸长了脖子问:“姐,那诗怎么说的来着?”
“啊?”令放下活计,抬起头稍微思索了一下,诵道:
“红枫秋水鲈鱼美,酒香鱼肥人酣醉,谁无归?渔翁扁舟篷底睡。”
这回年倒是听懂了,可惜壶里的并非那肥美的鲈鱼,而是杂鱼零碎儿,要吃那诗里的鲈鱼,得顺着江水走几千里,到夕的老家。
夕倒从未提起过她的故乡,年只能在她散落的画里,才能窥见一二:青瓦白墙,流觞曲水,石桥轻舟,烟雨水乡。秀丽的很,却和夕一样,瓷一般易碎。
“你有最喜欢的诗吗?”年问令。
她歪着头想了想:“现在的话,我最喜欢这首。”
“蹴注罢秋千,起来慵注整纤纤手。露浓花瘦,薄汗轻衣透。
见客入来,袜刬注金钗溜。和羞走,倚门回首注,却把青梅嗅。”
令念诗声音并不洪亮,但抑扬顿挫,让人忍不住一边听一边琢磨。
年目光一转,夕安安静静地坐在河边,细伶伶的腿像浸在水中的一节嫩藕,乌青的头发衬着清瘦的肩,散发出轻浅的光彩,让人觉得很耐看。
“长大了啊”年捧着鱼,心想。
上午的天气好的出奇,天空、山野、草木……一切都明丽地有些过分。
“诶,令姐,你的那个什么‘蹴罢秋千’什么的,写的啥来着?”年突然问
“那个啊?那不是我写的,是李清照。”
“李清照?”年咀嚼着这个名字“宋朝那个女词人?”
“对。”
年注意到夕,没继续问下去。她突然觉得,自己的妹妹,和李清照很像,不,至少大差不差。
夕像不像李清照是一回事,但她的的确确是个才女。她的字画算是全校,不,全县最好的一个。老师恨不得要将她的每一张帖子都用木框裱了挂到教室的最排头。县里的奖,市里的奖,省里的奖,她都拿了个遍。她的文章也很有来头,虽然尚有写青涩,却有一股十几岁的孩子根本不可能有的灵气和书卷气,读了叫人莫名地心头一怔。
这一切,直到夕抱着大红的奖状回来,年才知道。在此之前,她不太喜欢这个成天蹲在家里的妹妹,说她是个呆闷子。现在年知道,夕是个很有学问的呆闷子,看她的眼光里,也有了一份敬重。
年却并无什么才气,成绩虽然不差,但始终没什么彩头。上学上到一半,母亲过世,父亲远走,家里没了人,就回去看祖上留下的杂货店了,人倒精明,也不用像大多数辍学的孩子一样奔波劳累,也挺好。
尚蜀盆地将来自远方的湿气尽数锁在了山间,尤其是冬天,阴冷的风总会让夕手脚冰凉,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。令于是想了个办法,年体热,让姐妹两个睡一块捂捂。刚开始夕还挎着个脸老大个不乐意,不过几天,却又自己往年的被窝里钻了。每到这时候,年都能清晰的感受到夕的形体。四年来,二人从各自团据在被窝的一角,到现在,两个人已经快要挤不下了。
过了冬天,夕就十八岁,对每一个学子来说,都是最紧要的关头,考试、习题、作业……填满了夕所有的课余时间。年和令也只能悄悄为她泡上一壶茶,或者切上几瓣梨摆在一边,然后看着盘子里的吃食几个钟头也没有动过。
四月开始,杂货铺迎来了旺季,先是清明的白布和花圈,再是端午的粽叶和艾草。令整日忙着打理进货,顾不上夕,于是照顾她的责任便落到了年身上。二人待在一起的时间陡然增多了,却又碍于尴尬,反而说不上几句话。这种时候,年就会怀念无忧无虑的小时候。或许人愈加长大,便愈会觉得尴尬,然后愈加地怀念小时候。
院子里晾衣杆的影子越来越短,花间飞舞的蜂蝶,也换做树丛间喧闹的蝉儿。家家户户的门口,都插上了白色的茱萸花。
夕到城里赶考的日子到了,吃完早饭,令把夕几日前给夕订做的衣裳换上,合身的有些过分,却不是预想中阁中闺秀般的柔弱,而是带了几分锋芒。
六月中旬的清晨已经有些热了,一轮红日冒在山头,朝阳给夕镶上了一层金边,让年觉得很好看。夕就在田野上不显山不漏水地走着,迎着风,像一颗临风飘动着嫩叶的梧桐树,依旧很耐看。
走了两三里路,到了车站,年和令给她把行李搬上车。
“走了”
“晚上早点睡,夜里盖好被子,别贪凉。”
“知道了”
年和令目送着车子载着夕愈行愈远,最终消失在视线里。接下来的两天,夕将自己在城里度过。
很奇怪,夕已经走了,年却总是想起她细伶伶的手脚,她朦朦胧胧的吴侬软语,还有她那天早上在风里的背影……早上煮粥时年会想:夕的祛湿药,带够了吗?中午吃饭时,年会想:食堂的饭菜,夕吃的习惯吗?晚上躺在床上时,年会想:夕肯定又要手脚冰凉,睡不着觉了吧?
令的话也少了,只是不断忙于店里的活计,空下来时,便就着霜一般的月光,不停地喝酒,直到走起路来轻飘飘的,像在梦中。
两个沉闷的日夜后,夕回来了,年特地冒了雨,跑到县里的菜市场挑了一条最肥的鲈鱼蒸了,令也将多年藏着没舍得喝的酒拿了出来,让夕直纳闷是不是两个人有事要散伙了。
年和令都很兴奋,不停地聊天喝酒。
“妹妹,考的咋样?”
“嗯,挺好。”
“哎!我就说我们家夕这么有学问,肯定没话说!”
桌子上已经只剩下一盒骨头和硬壳,酒足饭饱,年夕令的脸上都露出了满足的红晕。
三人打了地铺,睡在一起,不大的被窝里,立马变得像上了热炕。窗外还下着雨,滴滴答答地落在错落的树丛上,竟能听出一点音律来,平日下雨,夕肯定是要腰酸脚痛的,但她今天睡得很安稳。
不知过了多久,雨已经停了。年忽的醒来,听见窗外有一只鸟在用雨水洗着身子,发出些细碎的动静。令也醒了,撑起身子要爬起来,二人低头一看,夕那张很清秀很耐看的脸,正在尚蜀朦胧的月光里,微微泛着红晕……